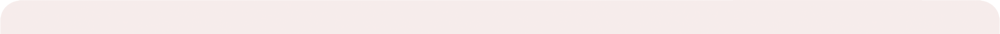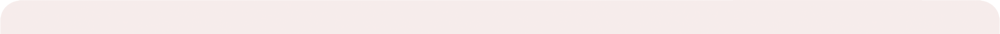1984年,中文系首届招生,先后经历了长沙水电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社科部、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世易时移,几经更名,但弦歌不绝,日日维新。如今,我们再回首这32年来的峥嵘岁月,中文系的名字就像五彩的旋律、多情的诗歌,这首歌她“带着梦里的心跳”,“象煞黑天的星星,越听越灿烂”,那是因为她浸透了一种永远感召我们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传承,我们愿意把这种精神和文化加以凝练、典藏和光大。
一、创业维艰
教育为本,百年大计。新时期办学创业之艰难,我以为莫过于长沙水电师院。水电师院的前身为长沙电力学校,以工科为主,地不过200亩,人不到1000人,在这个基础上办师范学院等于从头再来。学院于1983年开始筹建,1984年正式招收中文、数学两个专业的本科学生,共4个班140余生。
中文系创办初期,条件很差,举步维艰,全部家当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资料室。当时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占用两间教室、以工科书籍为主的图书室,在那种情况下,中文系的资料室对中文系的师生来说弥足珍贵。条件艰苦,但师生们干劲尤足,全系上下在首届系主任张实老师的带领下,乃承厥命,罗致英才,广收典籍,精心编篡,修订讲义,唯恐有所遗漏,以致遗恨。
师资方面,中文系在1984到1985年两年间,先后从南京、北京、武汉、兰州、长沙等地延聘了几十位中青年才俊:张实、杨翊强、丘良任、夏先培、谌东飚、陈其相、王德勇、靳绍彤、汪明凡、钟友循、罗明勋、甘云杰、樊锦鑫、张美娟、李维鼎、李中华,郑贱德、刘云夔、尹立晋、王东发、华德柱、孙亭玉,等等。可谓英才聚集,春风和煦,师生矻矻,锐意进取。
教材和教辅资料是当时最为困难的事情,由于筹备时间太短,许多课程都没有购买到满意的教材,怎么办?当时有句话非常感人:“没有条件,我们就自己创造!”于是,老师们决定自己刻写。学校打印室和系里资料室的工人不多,无法承担刻写教材这么繁重的任务,系领导就发动教师、发动字写得好的学生一起上,有的用机械打字机打印,有的用钢板刻写,少数资料送到校外影印,各种工具都用上,各色人员都调动。记得我班张署华同学因为字迹清秀工整,经常被老师请去刻写钢板,复印资料,经过全系上下几年的努力,中文系先后通过影印、打印、刻印的教材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四大本、《古汉语音韵学》两大本、《美学概论》一本、《中国图书分类法》一本。这些教材都是每天发一些散张,学生们自己保留,然后用牛皮纸或者挂历纸做封面装订而成。教辅材料尤其多,几乎每天上课前,老师都会发一些散装的教辅资料给我们,比如《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给战斗者》、《向太阳》、《血的春天》、《春鸟》、《将军,不能这样做》、《秩序》等等,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这些教材和教辅资料不但解决了我们当时之需,而且更加刺激了我们的求学欲望,刻板打字难免有错误之处,但面对刻印教材中不断出现的错误,我们都会记载在读书卡片上,课后就到系资料室、校图书室,乃至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加以订正,所以这些看似鸡肋的教材或教辅资料都成了我们手中的宝贝,有些还珍藏至今。
图书资料的短缺是我们的又一大难题,入学伊始,中文系就给我们下发了一本打印的小册子:《中文系学生阅读书目》,罗列必读书目有大几百种,可是大多数图书在学校图书室和系资料室无法找到,不得已,我们只得在老师的帮助下办理湖南省图书馆的借阅证,到省图书馆里去借阅图书,抄写资料。那段时间,如无特殊情况,我们每周至少要去省图书馆一次,正因为这样,我才会经常在省图书馆里遇见丘良任老师,不时得到他的指点,现在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邱老师也已去世多年,回首往事,真是慨叹世事无常呀。
二、书山云梯
就在这么艰难困苦中,老师们依然秉持教书育人的理念,不敢有丝毫懈怠。恩师夏先培是我大学时的班主任老师,更是引导我们进入学术殿堂的导师,他算起来应该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师出名门,并有良好的家学渊源,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博学、严谨、公正、宽宏,把学术当公器,视学生为己出,亲切慈爱,儒雅可范,他自己在一首感言诗中云“深宵斗室一灯黄,把卷神游兴味长。不慕荣华真富有,无分寒暑自温凉。千秋青史丰碑立,万里蓝空健翮翔。欲为苍生展襟抱,纷繁世事入文章。”这是他的真实写照。
夏老师引弟子进入学术之门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给我们八四级学生讲治学方法时,他给我们下发了两篇刻印的文章,一是程千帆先生的《詹詹录》,二是周勋初先生的《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程先生的《詹詹录》共二十节,篇名取自《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当然,这是程先生的自谦。夏老师在介绍此文时,强调学习汉语言文学要在典籍上下功夫,黄季刚先生认为欲成一代大师,须应精读八部书:《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要非常精熟,触类旁通,就能成为一代大师。对此观点夏老师是很推崇的,除此之外,夏老师引入《詹詹录》第十四节的观点:“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现在,我们学生聚在一起谈论夏老师时,总会说起夏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课文云云,其实,这一方面是夏老师小时候念书养成的习惯,同时也是对程先生观点的承继。除了背诵课文,夏老师还经常借程先生的观点,强调学术道德,强调严谨谦虚,等等。至于周先生的《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一文,1984年5月才成稿,1985年10月就被夏老师推介给我们。此文是周先生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评论文章,文章对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做了精辟的梳理和凝练,观点非常鲜明独到。夏老师在推介此文时,先从王国维先生的生平与贡献入手,引经据典,介绍了“敦煌学”、“甲骨学”、“乾嘉学派”,介绍了“清华四杰”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与成就,告诫我们治学要充分利用新材料,要言必有据,要实事求是,要学会分析与综合,要敢于“预流”、敢于“突破”。王国维承继的是乾嘉学派的传统,对于许慎、段玉裁等人在小学上的贡献,极为钦佩。但他并不像正宗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那样,拘守“师法”或“家数”。而是无所拘忌的进入“甲骨学”这一新开辟的学术阵地中去,终成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师祖。夏老师对王国维先生的推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王先生善于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善于从其他的学科中吸收养料。王国维先生在上海时先后读过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著作,1904年在康德理论的指导下,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是我国利用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随后,王先生放弃哲学而专攻文学,1908年成就了《人间词话》一书。夏老师认为成就大师,必须有兼收并蓄的态度和方法,必须有哲学的思辨力,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我们八四级的许多同学都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有过亲密的接触,我就半生不熟的读过《逻辑学》、《权力意志》、《存在与虚无》、《理想国》、《实践理性批判》等等,当然,由于当时就似懂非懂,现在,这些知识早就还给老师了。但不管怎样,读这些哲学著作,对提高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批判能力还是大有帮助的,这真得感谢夏老师当年的正确引导。
三、告慰恩师
“干戈涕泪动乾坤,漂泊西南到此村。潭府今真成乐国,能无一室驻诗魂?”
恩师丘良任先生有一大遗愿就是在岳麓山上建立杜甫草堂,希望杜甫也能像屈原、贾宜一样,诗魂永驻。
丘老师1984年从淮北煤炭师院到长沙水电师范学院任教,因时间较短,加之给我们上课不多,所以能够回忆起他的人可能不多,其时,丘老师应该是年近七旬,但依然精神矍铄,偶尔给我们八四级的学生上古代文学课,他的教学由于直观简明,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堂课是给我们讲《诗经》时(大概是讲座,记得不太准确了),他给我们挂了一幅他自己手绘的“诗经地理示意图”,这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了(当时学界评论似乎还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的这种授课方式,我们清楚了《诗经》的地理分布,加深了对《诗经》作品的理解,也影响了我后来的教学。
做科学研究可能是丘老师这段时间最主要的工作,在水电师院任教时,它主要在做杜甫研究。当时我国的研究条件都差,更何况我校刚刚创办,科研条件尤其落后,必要的设备缺乏,基本的图书资料不多,中文系也不能够很好提供这些科研条件,全系只有一台机械打字机和一台油印机,对于图书资料的处理大多是靠手抄心记。为了研究杜甫,无论寒暑,只要没有重要的工作占用时间,邱老师总是会提着一个褐色的、手工缝制的布袋子,搭乘两次公共汽车从金盆岭到省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为了考定杜甫终卒之地和晚年的诗歌创作,邱老师曾独身一人沿当年杜甫经行之处,从洞庭湖到湘江,一路实地考察,查阅当地的方志、族谱,拓印相关碑帖,跋山涉水,呕心沥血,终将杜甫晚年流寓湖南的诗作按月排列,编成《杜甫湖湘诗月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邱老师满怀深情的写了一篇文章:《岳麓应建杜甫草堂议》。杜甫是大历3年岁尽冬残时到湖南岳阳,次年春初到长沙,当时的长沙乃“清绝之地”,山河壮丽,楼阁峥嵘,田土肥美,民风淳朴,但杜甫在湖南毕竟垂老无依,又在舟中感染风疾,真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由于风疾不起,只好转帆去到昌江(现平江),竟以寓卒,魂灵与屈原为伍。杜甫热爱湖南,热爱湖南人民,赞美湖南的山水和淳朴的民风,同时也鞭挞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和冷漠,同情劳动人民大从的疾苦,如《祠南夕望》、《登岳阳楼》、《岁宴行》、《宿花石戍》、《送卢十四弟》等等。所以湖南人民也非常热爱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历代以来,湖南人民在平江、铜官等地建亭表达对杜甫的怀念之情,但随着时间的迁徙,这些纪念设施大多无存。因此许多的湖南有识之士都曾倡议在长沙建立草堂或专祠来纪念杜甫。清初长沙人秦文起曾写有五言律诗一首:“少陵游岳麓,丰彩映湖湘,应有精灵聚,非徒风雅长,林泉真可托,花鸟亦难忘,梦寐吾将老,高吟到草堂。”丘老师一生潜心研究杜甫,对杜甫充满深厚的感情,认为作为杜甫暂时栖身之地的四川都为他建有草堂,湖南“清绝之地”,杜甫欲终老于此,在洞庭潇湘间历经二年,留下诗作百余首,所以我们更有理由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上为诗人建立草堂,供后人瞻仰。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所以丘老师无不感慨:“衡嶽之巅朱凤鸣,洞庭雲水起湘灵,谁怜荒冢罗江上,寂寞千秋万代名。”又叹道:“干戈涕泪动乾坤,漂泊西南到此村,谭府今真成乐国,能无一室驻诗魂?”情也深深,意也真真,让人读后唏嘘不已。
九十年代末,我在财经系工作时,任蔼堂教授时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正值省政协征求提案,任教授问我是否有关于文化方面的提案,我想起了丘老师的遗愿,代任蔼堂教授写了一份《关于在长沙市西码头附近建杜甫专祠的提案》。该提案是否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不得而知,但也终将把丘老师的提议带到了省府决策的案桌之上,着实要感谢任蔼堂教授对湖南文化事业的支持。
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长沙人民终于在人民路西头的湘江边上建起了杜甫江阁,专门纪念这位唐代伟大的诗人,使得诗人的英魂能长驻湘江,与屈大夫为伴,与贾太傅为侣,这是诗人的幸事,也是长沙人民的幸事。不知道丘老师生前是否瞻仰过这座曾经为之鼓与呼的江阁没有,如若没有,但愿上苍有灵,让春风带着丘老师的英灵回到长沙,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杜甫江阁!
丘老师家学源远,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堪为后世表正,用夏先培先师在《电苑楼记》中的句子称颂他实为不过:“庶几上无愧于先哲,下无愧于后昆,外无愧于时代,内无愧于己心耶!”
陈浩凯
附件: